
商品分类
当前位置: 首页 > 文学艺术 > 文学 > 文学 > 逃离德黑兰-一个英雄的自白
- 编辑推荐语
-
2013年奥斯卡最佳影片;2013年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入围奥斯卡6项大奖的电影《逃离德黑兰》的原著。
全程揭秘CIA内幕,一个男人的责任、信心与勇气,一个段真实的历史,一个伟大的故事! - 内容提要
-
《逃离德黑兰(一个英雄的自白)》由安东尼奥·J·门德兹编著。
《逃离德黑兰(一个英雄的自白)》简介: 1979年11月4日,六位美国外交官设法逃出了激进分子围攻的美国大使馆。其余人员遭到扣押,长达444天。六位逃亡者在加拿大使馆留宿了两个多月,直到中央。睛报局展开冒险营救行动。
门德兹是中央情报局顶级“偷越封锁线”特工。他想出了勇敢的计划,断定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营救行动需要大胆的掩盖。他在真正的好莱坞制片人协助下,伪称拍摄科幻电影《阿尔戈号》。这项瞒天过海的计划面面俱到。甚至在好莱坞发出了各式各样的假广告。他和他的团队接下来为六位外交官制作假档案,冒充加拿大电影摄制组成员,在伊朗寻找合适的场地。
然后是危险的部分:门德兹和另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在加拿大政府的协助下,进入伊朗境内,在进行了充分的说服和精心的准备之后,门德兹带领他的“摄制组成员”终于通过层层关卡,在德黑兰机场登机。同一天,加拿大驻伊朗使馆关闭,加拿大大使也立即返国。
19世纪80年代,《阿尔戈号》的故事一直不为人知晓。因为考虑到剩余人质的安危。CIA和加拿大政府也对整件事情的过程讳莫如深。直到1 997年,CIA才完全公开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门德斯亲自撰写了整个营救过程的详细报告——不过,伊朗方面并不认为CIA说了实话…… 《逃离德黑兰:一个英雄的自白》是2013年金球奖最佳影片、奥斯卡获奖电影《逃离德黑兰》的原著。
电影的导演本阿弗莱克称赞它是“一个伟大的故事”。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男人的勇气与责任,以及在绝境中看到希望的乐观精神。为了六个素不相识的外交官,门德兹以身涉险,深入敌国,并且采取了最大胆的营救计划。他本可以放弃这次行动,但他最终坚持做完了该做的事。阅读本书,你会感受到人性的光辉力量,这种力量超越政治与国界,与每一个人的心灵息息相通。你所收获的绝不仅是一个好看而真实的故事,更是坚持信念,在无望的现实中继续奋斗的勇气,承担起生命的责任的坚强力量。
- 作者简介
-
美国中情局伪装部门负责人,电影《逃离德黑兰》男主角原型。 1965年加入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部门,从事秘密工作25年,参加过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一些秘密活动。1980年1月,他在伊朗危机中营救6位美国外文官,获得“勇敢情报之星”的奖励。30多年后,这段经历被改编成了电影《逃离德黑兰》。 1997年,他获得“开拓者”大勋章。在最初为中情局工作的上万人中,只有50人获得这种殊荣。勋章承认他“以其行动、榜样和主动精神……塑造了中央情报局的历史”。 著有《伪装大师》《间谍生涯》等书。 马特·贝格里欧(Matt Baglio)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他的著作《仪式:现代驱魔人》。The Rite:The Making of A Moder”Exorctst)被改编为电影,由著名男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于2011年上映。
- 目录
-
楔子 第一章 革命的伊朗 第二章 中情局 第三章 鹰爪行动 第四章 无处可逃 第五章 救命稻草 第六章 他山之石 第七章 动员令 第八章 掩护身份 第九章 伪装大师 第十章 好莱坞 第十一章 准备材料 第十二章 中转站 第十三章 伊朗现场 第十四章 预演 第十五章 背水一战 第十六章 荣光 楔子 第一章 革命的伊朗 第二章 中情局 第三章 鹰爪行动 第四章 无处可逃 第五章 救命稻草 第六章 他山之石 第七章 动员令 第八章 掩护身份 第九章 伪装大师 第十章 好莱坞 第十一章 准备材料 第十二章 中转站 第十三章 伊朗现场 第十四章 预演
- 前言
-
那一天是1979年的12月19日,周六。傍晚,我正在工作室里绘画。窗外,落日依山而下,余辉映出一道长长的暗色光影,如同帷幕一般盖住了山谷。
本周早些时候,我收到了美国国务院下发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包含一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六名美国外交官逃离了被激进分子占领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躲进了加拿大驻伊朗大使肯·泰勒及其高级移民官约翰·希尔唐的府邸。
一个多月以前的11月4日,一群伊朗激进分子袭击了美国位于德黑兰的大使馆,扣押了六十六名美国人质,随即在全城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搜捕美国人的行动。他们指控美国人暗中从事“间谍”活动,试图破坏这个国家兴起的伊斯兰革命。
在大使馆被占领时,我已是中情局技术服务办公室下属的全球伪装行动部门的负责人。在过去十四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众多秘密行动,为特工和情报官员提供伪装支持,并协助营救“铁幕”背后的叛逃者和避难者。大使馆遭到攻击之后,我和我的团队立即行动起来,为潜入伊朗的先遣队准备各种所需的伪装品、虚假文件以及不同化名的掩护身份。而就在准备期间,我们收到了国务院的备忘录。
对于这六名美国人,国务院似乎采取了一种观望策略。在我看来,这是很有问题的。我最近刚去过一次伊朗,对于那里的危险,我有亲身经历。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眼线,时时刻刻注视着你,搜寻着你。在任何时候,你都有可能会被发现。
这六个人已经躲藏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还能够坚持多久?如果这六名美国人必须逃跑,他们会去哪里?在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外,每天都聚集着数千名群情激愤的伊朗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抓,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会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处死。
我一直对我的团队讲,撤离行动有两种:一是遭到恶意追捕,二是未遭恶意追捕。我们不能等到这六名美国人四处逃亡时才去营救他们,因为那时候我们几乎不可能将他们安全救出。
电台正在播放歌曲《风雨无阻》。在创作时,我经常会收听音乐。对我来说,音乐几乎与光线同等重要。
我的绘画生涯始于孩提时代,在1965年加入中央情报局时,我已经是一名艺术家了。至今,我仍认为我首先是一名画家,其次才是一个间谍。在中情局工作期间,绘画一直都是我纾解个中压力的出口。偶尔,我会对某些官僚的古怪行为感到气愤,甚至到了想掐死他们的地步,但如果让我回到工作室,拿起画笔,那么所有这些敌意都会烟消云散。
那天下午的创作,源于与我工作相关的一个词语:“狼雨”。在一个令人压抑、沮丧、阴暗冬日夜晚,与窗外的茂密丛林对话。它传递的是一种我无法言表的悲伤,但直觉告诉我,我能把它画出来。
如果创作顺利,那么我的大脑就会迅速进入一种“阿尔法”模式:主观的、富于创造性的右脑就会实现突破。爱因斯坦曾对天才下过一个定义:天才并不是你比所有人都聪明,而是你已经做好了获取灵感的准备。对我来说,这就是“阿尔法”的定义。我会通过绘画来纾解工作压力,并通过这种创作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会让你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已经做好了获取灵感的准备。
在对油画布的底层色着暗釉时,我的思绪迅速发生转变,一个初步的计划开始在脑海中显现出来。我们不仅要为这六名美国人伪造新的身份,提供伪装支持,而且要派人潜入伊朗,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对他们的撤退能力进行评估。
我的儿子伊恩走进了工作室。他以一种艺术家特有的眼神审视着这幅画作,而当时他只有17岁。“很好,爸爸。”他一边说着一边后退一步,以便找到更好的角度,“但这需要多加一点蓝色。”他指的是狼的眼睛。
“快离开这儿,伊恩。我大概三十分钟后去吃饭。告诉你妈妈,好吗? ”我说。
电台中传出了埃拉的一首歌曲——《只是其中之一》。伴随着歌声,我也开始用松节油清洗我的画笔,并给油画盖上防护罩。
无数问题开始涌入我的脑海。我如何说服这六名无辜的、未接受过隐秘行动训练的美国外交官,让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成功逃出伊朗?我需要编造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足以让几个“外国人”有理由在这种时候来到伊朗?我虽然组织过数十次的撤离行动,但这一次可以说是我所遇到的最具挑战的任务之一。
我关掉了收音机和电灯,静静地站在黑暗中,窗外一片漆黑,只有暖房里的枝形吊灯散发出朦胧的光。我思忖道,谍报行动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对于适当的、专业的谍报行动,国际上是有一套交涉规则的;但就目前伊朗的革命政府而言,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任何规则。
-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
第一章革命的伊朗 1979年11月4日,对于前去大使馆上班的美国人来说,这天的清晨与往常一样。大使馆临时代办布鲁斯·兰根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了一场晨会,之后和维克·汤姆塞斯以及迈克·豪兰赶往伊朗外交部,前去讨论美国驻伊朗军事人员的外交豁免权问题。
上午十点钟刚过,无线电网络传出呼叫声:“注意!注意!所有海军陆战队员,一号位集合。”发出呼叫的是大使馆的安保主管阿尔·戈拉辛斯基。这一刻,大量“激进学生”冲破大门,涌入美国大使馆。
大使馆的新闻处就位于正门附近的停车场一侧。有人切断了门上的环形锚链,大批游行示威者蜂拥而入,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她们举着上面写有“不要害怕,我们只是想进来”的标示牌。
约翰·格雷夫斯是最先看到激进分子冲进使馆区的人之一。他是美国大使馆的公共事务官。靠近窗户朝外望去,他看到一名激进分子走向一名负责保护使馆的警察,然后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对于这一幕,格雷夫斯并不感到惊讶。
随着涌入使馆区的激进分子越来越多,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开始慢慢反应过来。在当时的伊朗,游行示威活动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而 “美国去死”、“打到沙赫”等口号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喊,所以在使馆内部工作的美国人最初还以为这是外面的“背景噪音”。
现在,只需几分钟的时间,激进分子便可包围整个办公楼。工作人员和使馆外交人员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的站在椅子上朝窗外望去,有的则聚集在警卫室,通过那里的闭路监控器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使馆区挤满了激进分子,他们挥舞着标语并高喊:“我们只是想进来!”然后,一个接着一个的闭路监控器出现空白画面,因为摄像头已经被示威者从墙上拽下来了。
大多数使馆工作人员都显得很平静,有的甚至还表现出了厌烦的情绪。他们似乎认为,这些学生只是闯入大使馆喊喊口号而已,到时候他们自然会离开。闯人者大喊着:“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只是想进来!” 在他们中间,有的人还拿着扩音器,声浪一次高过一次。
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这并不是一次狂热的抗议游行,而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袭击行动。这些自称为“伊玛目的门徒”的学生早在多日前就已经对大使馆踩点,并绘制了详细的地图。他们裁剪布条,为可能抓获的人质准备了近一百条蒙眼布;他们甚至还为这些人质准备了食品。
他们精心将发动袭击的时间选在“国家学生日”。国家学生日是为了纪念一年前在德黑兰大学游行示威时被沙赫武装力量杀害的学生而设立的,那次游行活动吸引了数百万名学生参加,而真正的策划者则在庞大人群的掩护下发动攻击。在第一波冲人大使馆的人群中,女性占有绝对多数,这显然也是有意而为,因为在激进分子看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应该不会对女性示威者开火。
部分激进分子还持有自行车锁链、木板乃至铁锤等简易武器。另有少数人持有手枪,这与后来宣称此次袭击完全是非暴力行动的说法相左。
他们的计划是占领大使馆三天,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沙赫和美国的种种不满。就主要目的而言,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攻击行动把温和的巴扎尔甘政府①拖人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进而削弱它的地位。如果巴扎尔甘派人营救这些美国人,那么伊朗人就会把他及其政府中的温和派人物视为 “西方的傀儡”。
戈拉辛斯基发出呼叫后,海军陆战队迅速集结。在进驻使馆办公楼之后,他们迅速进入战备状态,装好子弹并占据有利位置,肾上腺素不断上升,有的人似乎还渴望一战。其中有一名队员就趴在办公室的地板上,身边摆满了弹药。他紧盯着窗外,手中的霰弹枪已经做好了发射的楔子 那一天是1979年的12月19日,周六。傍晚,我正在工作室里绘画。窗外,落日依山而下,余辉映出一道长长的暗色光影,如同帷幕一般盖住了山谷。
本周早些时候,我收到了美国国务院下发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包含一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六名美国外交官逃离了被激进分子占领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躲进了加拿大驻伊朗大使肯·泰勒及其高级移民官约翰·希尔唐的府邸。
一个多月以前的11月4日,一群伊朗激进分子袭击了美国位于德黑兰的大使馆,扣押了六十六名美国人质,随即在全城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搜捕美国人的行动。他们指控美国人暗中从事“间谍”活动,试图破坏这个国家兴起的伊斯兰革命。
在大使馆被占领时,我已是中情局技术服务办公室下属的全球伪装行动部门的负责人。在过去十四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众多秘密行动,为特工和情报官员提供伪装支持,并协助营救“铁幕”背后的叛逃者和避难者。大使馆遭到攻击之后,我和我的团队立即行动起来,为潜入伊朗的先遣队准备各种所需的伪装品、虚假文件以及不同化名的掩护身份。而就在准备期间,我们收到了国务院的备忘录。
对于这六名美国人,国务院似乎采取了一种观望策略。在我看来,这是很有问题的。我最近刚去过一次伊朗,对于那里的危险,我有亲身经历。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眼线,时时刻刻注视着你,搜寻着你。在任何时候,你都有可能会被发现。
这六个人已经躲藏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还能够坚持多久?如果这六名美国人必须逃跑,他们会去哪里?在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外,每天都聚集着数千名群情激愤的伊朗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抓,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会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处死。
我一直对我的团队讲,撤离行动有两种:一是遭到恶意追捕,二是未遭恶意追捕。我们不能等到这六名美国人四处逃亡时才去营救他们,因为那时候我们几乎不可能将他们安全救出。
电台正在播放歌曲《风雨无阻》。在创作时,我经常会收听音乐。对我来说,音乐几乎与光线同等重要。
我的绘画生涯始于孩提时代,在1965年加入中央情报局时,我已经是一名艺术家了。至今,我仍认为我首先是一名画家,其次才是一个间谍。在中情局工作期间,绘画一直都是我纾解个中压力的出口。偶尔,我会对某些官僚的古怪行为感到气愤,甚至到了想掐死他们的地步,但如果让我回到工作室,拿起画笔,那么所有这些敌意都会烟消云散。
那天下午的创作,源于与我工作相准备。P5-7 关的一个词语:“狼雨”。在一个令人压抑、沮丧、阴暗冬日夜晚,与窗外的茂密丛林对话。它传递的是一种我无法言表的悲伤,但直觉告诉我,我能把它画出来。
如果创作顺利,那么我的大脑就会迅速进入一种“阿尔法”模式:主观的、富于创造性的右脑就会实现突破。爱因斯坦曾对天才下过一个定义:天才并不是你比所有人都聪明,而是你已经做好了获取灵感的准备。对我来说,这就是“阿尔法”的定义。我会通过绘画来纾解工作压力,并通过这种创作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会让你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已经做好了获取灵感的准备。
在对油画布的底层色着暗釉时,我的思绪迅速发生转变,一个初步的计划开始在脑海中显现出来。我们不仅要为这六名美国人伪造新的身份,提供伪装支持,而且要派人潜入伊朗,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对他们的撤退能力进行评估。
我的儿子伊恩走进了工作室。他以一种艺术家特有的眼神审视着这幅画作,而当时他只有17岁。“很好,爸爸。”他一边说着一边后退一步,以便找到更好的角度,“但这需要多加一点蓝色。”他指的是狼的眼睛。
“快离开这儿,伊恩。我大概三十分钟后去吃饭。告诉你妈妈,好吗?”我说。
电台中传出了埃拉的一首歌曲——《只是其中之一》。伴随着歌声,我也开始用松节油清洗我的画笔,并给油画盖上防护罩。
无数问题开始涌入我的脑海。我如何说服这六名无辜的、未接受过隐秘行动训练的美国外交官,让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成功逃出伊朗?我需要编造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足以让几个“外国人”有理由在这种时候来到伊朗?我虽然组织过数十次的撤离行动,但这一次可以说是我所遇到的最具挑战的任务之一。
我关掉了收音机和电灯,静静地站在黑暗中,窗外一片漆黑,只有暖房里的枝形吊灯散发出朦胧的光。我思忖道,谍报行动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对于适当的、专业的谍报行动,国际上是有一套交涉规则的;但就目前伊朗的革命政府而言,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任何规则。
……
商品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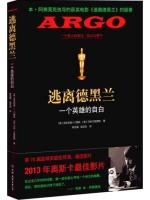

 有限责任公司
ICP备案证书号:
有限责任公司
ICP备案证书号:
